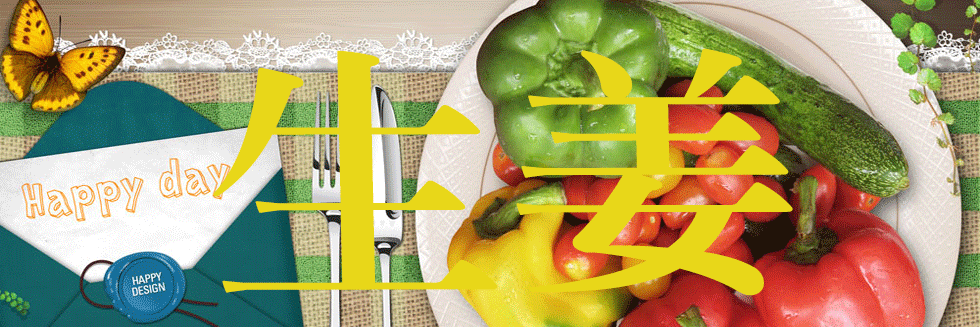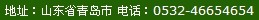|
张骞出使西域,将大蒜引入中原 晋代的崔豹在《古今注》里提到过一种卵蒜:“卵蒜也,俗人谓之小蒜。外国有蒜,十许子共为一株,箨幕裹之尤辛于小蒜,俗人呼之为大蒜。” 根据其记载,中国传统的蒜种为卵蒜,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山蒜、小蒜。至于大蒜,则是外来物种。汉朝时张骞出使西域,将大蒜引入了中原。由于大蒜的产量高、蒜头大,所以很快便传播了起来。 《后汉书》有个记载,说的是东汉的李恂由西北来山东任刺史,带来了一些胡蒜种,然后在官府后园开了一块地种蒜,收获了之后送了一些给下属官员。李恂种的这种胡蒜,便是我们如今熟知的大蒜。 到了魏晋时期,大蒜已经传播很广了。《三国志》里还有华佗用蒜治病的故事。有一回华佗走在路上,看到一个人生病,想要吃东西却不能下咽。华佗告诉他们:“刚才路边有卖饼的人家,有蒜泥和醋,你向店主买三升喝下去,病自然就会好了。”他们立刻按照华佗所说的去做,病人喝下后吐出一条寄生虫,病就好了。 有的人觉得蒜的味道大,吃蒜容易口臭,影响人设或形象。但是西晋的知名美男子潘安倒是不太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。他写过一篇《闲居赋》,在总结自己官场生涯的同时表达了对闲居的向往。其中就提到:“菜则葱韭蒜芋,青笋紫姜。”葱姜蒜韭芋,一样不落,而且还说:“堇荠甘旨,蓼荾芬芳。”其中的“荾”是香菜,意思是堇菜荠菜甜美可口,蓼菜香菜香美芬芳!吃完说不定还得感慨一声:香菜配大蒜,味道真不赖! 南北朝的《齐民要术》里还记录过种蒜的方法,而且总结过相关经验:“蒜宜良软地。白软地甜美而科大,黑软及刚强地,辛辣而瘦小。”还提到了一种“八和齑”的调味品,即用蒜、姜、橘(皮)、白梅等八种物料经清洗处理后捣烂调制成。而且,蒜还是制作生鱼片的必备调料,当时有道生鱼片叫作“金齑玉脍”,调料中的蒜能去腥调味,不可或缺。 袁枚吃蒜有心得,李化楠甚至更胜一筹 唐朝的吃蒜风气很盛。唐朝诗人高适写道:“清酒浓如鸡,臛豚与白羊。不论空蒜酢,兼要好椒姜。”“酢”有酸味或者醋的意思,“蒜酢”估计是腌制的酸大蒜。此外,唐朝诗人易静还有“独头大蒜乌梅肉”之句。 唐朝的《广古今五行记》里有一个故事,说有个洛阳和尚嘴馋,找到当地的司户唐望之家,想着吃鱼。唐望之正想准备,和尚又问有没有蒜。唐望之回答说蒜没了,得再去买。和尚说蒜没了就拉倒,不吃了。和尚想吃鱼,因为无蒜佐味而放弃。唐朝的花和尚不少,唐朝诗僧寒山也曾在自己的诗里记录过吃肉的情景:“蒸豚揾蒜酱,炙鸭点椒盐。”蒸大肉要蘸着蒜酱才好吃。 宋代的厨娘吴氏在《中馈录》里也记载过一些蒜香菜,比如“蒜瓜”,即以秋天的小黄瓜为食材,用白灰、白矾水焯过后,把水控干,用半两盐腌一晚上。之后再用半两盐,三两大蒜瓣捣成泥,和黄瓜拌匀,然后倒进腌水中,用熬好的酒、醋浸泡,放在凉地方。蒜冬瓜、蒜茄子的制作方法也是如此。此外,《中馈录》里还有一道“蒜梅”,即以特定方法对青梅和大蒜进行浸泡腌制。 清代的吃货袁枚对于吃蒜有自己的心得。他在《随园食单》里强调过:“凡一物烹成,必需辅佐……其中可荤可素者,蘑菇、鲜笋、冬瓜是也。可荤不可素者,葱韭、菌香、新蒜是也。”在他看来,新鲜大蒜适合搭配肉类吃,而不合适搭配蔬菜。比如在制作油灼肉和炒肉丝的时候,都得搭配蒜,烹甲鱼时也得加蒜。 同样是清代乾隆年间的美食家,李化楠就比袁枚更喜欢吃蒜,《醒园录》里记载过他的一些食谱,比如蒸猪头法:猪头刷割极净,里外用盐擦遍腌制,到热水中滚三五滚,捞起用大蒜捣极细烂擦上,再上蒸笼内,蒸至极烂。关东煮鸡鸭法也得加大蒜瓣十数枚。此外,炖脚鱼和煮鲍鱼时都少不了蒜。 李化楠的食谱里还有现代人常用的一种炒菜方法,例如在炒鳝鱼和煮鱼翅时会用到:麻油下锅后先加入蒜下锅,连炒数遍,再加入其他食材。更关键的是,李化楠的食谱里专门记载了“腌蒜头”的法子:新出蒜头去杆及根,用清水泡过后洗净捞起,用盐水加醋腌之。 来源:北京青年报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lianjiangliuxue.com/jsp/jsp/18092.html |
当前位置: 姜_姜食品_姜挑选 >趣历史丨古人吃蒜哪家强
时间:2024/7/30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辣子鸡的制作方法,大厨教你简单7步,轻松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